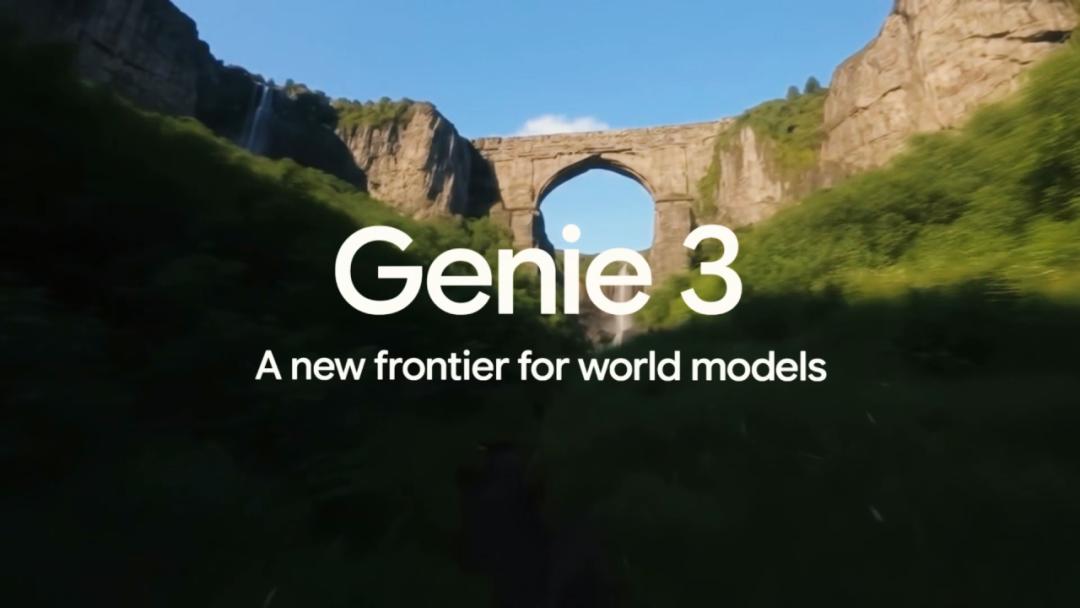机器人不再是“演员”,王兴兴:机器人打工也要交税
短短两周内,从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,人形机器人的热潮席卷全国。
8月8日~12日,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再现“人从众”景象,赶来看人形机器人表演的观众摩肩接踵,200多家企业、1500多件展品,50家整机人形机器人厂商同台飙戏:从仿生蜜蜂的灵活飞行,到人形机器人熟练叠衣、分拣货物,再到核心零部件如高精度关节模组的亮相……
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地撕下了“大号遥控玩具”的标签,开始比拼“干实事”的落地能力,展台更是干脆设置成养老院、商超、工厂流水线等不同场景。
展台不再是T台,机器人的身份开始从“演员”变成“打工人”。
变化背后,有几个鲜明的信号。
厂商开始“标价”了。宇树的R1人形机器人,标价3.99万元;架子鼓机器人价格为25.9万元;一个名叫“美膳狮2K”的机器人售价为49.8万元……尽管这些机器人能否真正进入消费级市场还需存疑,但至少说明具身智能的关键零部件供应、制造工艺和组装效率都有所突破,具备了规模化生产的条件。
宇树R1人形机器人
订单真有了。以前的展会上,机器人企业参展的目的大多只是展示,而今年真有买家带着采购单来了。官方数据显示,大会期间共售出机器人及相关产品1.9万台,销售额超2亿元,这说明B端市场开始认真考虑把机器人请回去上班。
场景不再是精心编排的秀,而是“原汁原味”的真实工作,这些机器人现场叠衣服、点胶、搬货、分拣,尽管时延、精准度以及自主操作还是常常会有Bug,但比起半年前已有大幅提升,具身智能“智能涌现”的拐点或许会进一步加速到来。
产业链正在围绕具身智能重塑。中国信通院发布的《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研究报告(2024年)》预计,2045年后,我国在用人形机器人将超过1亿台,整机市场规模可达约10万亿元级别。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也表示,机器人产业上半年平均增速达50%~100%,中国企业占全球出货量的70%以上。高速发展的市场直接导致其他行业开始加速进入具身智能领域。激光雷达厂商从汽车向机器人转移,禾赛JT128便搭载在机器狗上,汽车集团也纷纷入局,特斯拉早在多年前便开始打样,国内车企亦步亦趋,广汽集团便推出了GoMove轮椅机器人,具身智能或许是各家企业远超汽车的“第二增长曲线”。
一旦跨界者入场,说明这条赛道已经嗅到了“大生意”的味道。
然而,要实现王兴兴提出的“机器人GPT时刻”——机器人能在陌生会场听懂“把水带给某位观众”的随机指令并流畅完成任务—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这不仅要求AI具备更强大的泛化能力,也对硬件的可靠性和成本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目前宇树实验室的测试数据显示,现有模型在陌生环境执行“递水”任务的成功率不足30%。
核心问题仍然是人形机器人负责运动控制的“小脑”和负责感知决策的“大脑”能力不足,而在发展路径上,各家企业也不尽相同。
王兴兴认为,当前具身智能大模型的发展阶段类似“GPT智能涌现前的2~3年”,基础模型的泛化能力不足,采集数据并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,解决方案应该是“小样本高泛化”范式:也即少量数据训练高算法模型,非纯数据驱动。
王兴兴所针对的应该是当前主流的VLA(视觉——语言——动作)模型,这是一种将视觉感知、自然语言理解与动作决策统一到同一框架的人工智能模型,需要大量预采集数据训练,然后让机器人学习后形成决策闭环。但他认为,数据采集的质量和数量都远远不够,即便在VLA模型基础上加入强化学习训练,仍不够用,模型本身还需要进一步升级和优化。
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认同这个观点。星海图联合创始人许华哲认为,模型不够用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数据不够。没有数据,模型能力永远无法从59分突破到90分,数据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下限和基础。
大会上,机器人铺床卡壳、运动中断,但能“意识到失败”并尝试新解法,这正是数据驱动闭环的亮点,也暴露了模型智能泛化的不足。
因此,谷歌刚刚发布的世界模型Genie 3被不少人看好。它可以先生成虚拟物理世界,再驱动机器人动作。不同于OpenAI的Sora,Genie 3是第一个允许实时交互的世界模型。王兴兴认为,谷歌这条视频生成技术路线的收敛速度和成功概率可能会比VLA模型更高。
如果Genie 3出现“GPT时刻”,或许意味着未来机器人可以先在虚拟工厂里学会一切,然后再到真实世界“直接上岗”。
无论如何,乐观者和谨慎者对于人形机器人进入家庭的时间估算,最远都不超过10年:大模型、硬件迭代、产业链能力……这些制约因素尽管还面临诸多挑战,但没有人怀疑,这些问题将很快会被解决。
只是,十年后机器人真能成为人类的伙伴吗?事实上,和自动驾驶一样,技术先行者的乐观往往会在伦理和政策前碰壁。
当人形机器人从简单的工具,进化到拥有强大运动能力和自主决策能力的具身智能体时,它需要回答的问题不再是“会不会坏”,而是“会不会犯错”。
如果它采集了家庭成员的面部、声音、健康数据,这些数据的存储和使用是否安全?它在家中行动时,万一与主人发生碰撞或造成损伤,责任算谁的?它是否会被黑客入侵,变成一台“被远程操控的机器?”在法律上,我们需要重新定义“人形机器人造成的损害责任归属”;在政策上,要建立家庭级机器人的准入与备案制度;在伦理上,则必须明确它们在儿童、老人、卧病等弱势人群场景下的行为边界。
王兴兴在这个问题上浅尝辄止,他提出的“机器人打工也要交税”,本质上已经将其等同于和人一样的劳动者。这种身份的认同,随着机器人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,可能出现的社会结构、就业心态以及经济形态的变化,都无法预知。
未来,进入工厂和家庭的不只是机器人,而是一道人机共存的伦理考题。届时再谈起人形机器人,我们关注的,或许不再是科技带来的各种“哇喔”,而是它如何不会成为人类走向终点的句号。
图片/ 宇树 银河通用机器人 谷歌 IT时报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“IT时报”(ID:vittimes),作者:郝俊慧,36氪经授权发布。